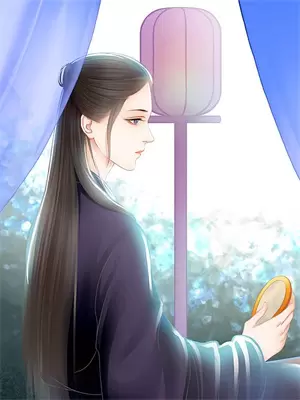阿妈失踪那天,村里人都在骂她跟野男人跑了。直到警察从后山挖出七具女尸。
每具尸体的脚踝上,都系着阿妈编的红绳。而我的枕头里,藏着她用血写的信:装瘸十年,
该逃了。————————————阿妈的手指很长,在昏黄的煤油灯下,
像两截嫩白的细葱。她总爱在一天劳作后,就着那点微弱的光,用买来的最便宜的红棉线,
编一种复杂的平安结。线在她指间灵活地穿梭、缠绕,最终形成一个紧密、好看的结。
她一边编,会一边低声哼着不成调的曲儿,那声音软软的,像是山涧里淌过的溪水,
能暂时洗去白日里的疲乏和爹落在她身上的阴沉目光。“丫头,过来,”她朝我招手,
把我拉到跟前,把新编好的红绳系在我瘦小的脚踝上,打上一个死结,“系紧了,
菩萨才能看见,才能保佑我们丫头平平安安,无病无灾。”她的指尖带着一点凉意,
划过我的皮肤,眼神里有种我那时还看不懂的、沉甸甸的东西,像是祈求,
又像是某种坚定的承诺。但她从不把红绳系在我手腕上,说手腕露在外面,容易磨断,
只有系在脚踝上,藏在裤管里,才最稳妥,最长久。村里的女人偶尔见了,会打趣:“秀英,
又给你家丫头系‘护身符’呢?编得可真精巧。”阿妈便垂下眼,腼腆地笑笑,
手下编结的动作更快了:“闲着也是闲着,编着玩儿,图个心安。”那时的我,
只知道这红绳是阿妈给的,带着她身上的皂角清香和指尖温度,是黑沉沉的夜里,
唯一一点暖色的念想。我瘸着腿走路时,能感觉到那根细细的红绳摩挲着脚踝的皮肤,
是阿妈无声的陪伴。可我从未想过,这看似柔弱的红绳,
有一天会变成撕裂一切平静的、染血的烙印。阿妈失踪那天之前的晚上,她给我洗脚时,
还摸了摸我脚踝上那根已经有些褪色的旧红绳,轻声说:“明天阿妈给你换根新的。
”她的声音比往常更轻,像羽毛拂过,眼神飘向窗外黑黢黢的大山,
里面有我看不分明的、水光一样的东西在晃动。然后,天亮了,她就不见了。
村口的老槐树下,唾沫星子混着旱烟的辛辣,能把人腌入味。“我就说那女人不是个安分的!
瞧她那对招子,水汪汪的,天生就会勾魂!”“平时装得一副老实相,啧,到底是忍不住,
跟野男人跑了!”“苦了根生哦,还有他家丫头……”“他家丫头?嘿,没准儿就是个野种!
”我靠着褪了色的门框,木木地看着那些一张一合的嘴,像看着一池塘鼓噪的蛤蟆。
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眼睛发疼。爹蹲在屋檐下,脑袋埋在膝盖里,
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呛人的旱烟,灰白的烟灰落在他开了口的胶鞋上,烫出几个小小的黑点。
他没像往常那样,抄起棍子或者鞋底把那些嚼舌根的人骂回去,只是沉默着,
那沉默里有一种奇怪的虚软,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有人拍了拍我的头,是邻居李婶,
她塞给我一个还温乎的烤红薯,脸上的褶子里堆着恰到好处的同情:“丫头,
别听他们瞎嚼蛆,你阿妈她……唉,许是有什么说不出的苦衷。”她叹着气,眼神却像钩子,
想从我脸上刮出点别的什么。苦衷?我捏着手里温热的红薯,指甲掐进软烂的皮里,
留下几道深色的印子。在这山里,女人的“苦衷”最后都变成了河里的泡影,后山的黄土,
或者别家炕上捂不住的呻吟。阿妈能有什么例外?她那双编出无数平安结的手,
终究没能编好自己的命运。她不就是嫌弃这个家穷,嫌弃爹没本事,嫌弃我是个拖油瓶,
所以跑了么。就像他们说的那样,跟野男人跑了。这山里,跑掉的女人不止一个,
她们都成了男人下酒的骂料和女人眼底的警钟。可我脚踝上那根她亲手系上的旧红绳,
却像一道渐渐收紧的箍,勒得我透不过气。阿妈不见的第五天,村子表面的那点同情假象,
就像被太阳晒干的露水,迅速蒸发了。那些黏腻的、探究的目光,
越发不加掩饰地落在我身上。我去井边打水,隔壁的王婆凑过来,
枯爪一样的手捏了捏我的胳膊,对旁边洗衣裳的妇人啧啧道:“瞧这丫头,瘦是瘦了点,
骨架倒还匀称。秀英跑了,留下这么个‘小包袱’,根生一个大男人可怎么弄?
”那妇人甩了甩手上的水珠,斜眼瞅我:“可不是嘛,半大的丫头,吃穷老子。要我说啊,
女孩子家家的,读什么书?认得几个字还能飞出这山窝窝去?早点找个婆家才是正经,
还能换点彩礼贴补家里。”她的话像裹着糖衣的砒霜,听起来像是为我爹打算,
字字句句却都在把我往某个既定的深渊里推。“婆家?”王婆瘪着嘴笑,
露出稀稀拉拉的黄牙,“也得有人敢要啊。她阿妈那个样子……哼,
谁知道这丫头骨子里随了谁?再说了,腿脚还不利索。
”她浑浊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我微跛的左腿,那里面没有怜悯,
只有一种衡量货物瑕疵般的挑剔。我低着头,用力拽着井绳,木桶磕在井壁上,
发出沉闷的响声。她们的话像针,密密麻麻地扎在心上,但我不能哭,也不能反驳。
阿妈说过,在这种时候,沉默和顺从是最好的盔甲。李婶依旧隔三差五送来点吃的,
有时是一把青菜,有时是几个土豆。她不再提阿妈,反而开始跟我爹搭话。“根生兄弟,
不是嫂子多嘴,你这日子往后可难了。”她一边帮我爹缝补一件破旧的外套,一边叹气,
“屋里没个女人操持,不像个家。丫头也一天天大了,总跟你一个大老爷们住一起,不像话。
”爹闷头抽烟,不吭声。李婶压低了声音,但我蹲在灶膛前烧火,
那声音还是丝丝缕缕地钻进耳朵:“……后山梁子那边,老刘家前年买来的那个媳妇,
听说最近闹得厉害。要我说,当初就不该找那种性子烈的,费钱还不省心。
还是得找知根知底的,或者……像你家丫头这样的,从小看着长大,性子软和,
好拿捏……”爹抽烟的动作顿住了,烟雾后面,他的眼神复杂地闪烁了一下,
很快又恢复了死寂。他没接话,但也没打断李婶。我的心,在那一刻像被浸入了冰水里。
李婶的话,不再是简单的闲话,它指向了一个模糊却恐怖的未来。知根知底?性子软和?
好拿捏?这些词组合在一起,像是在为某种交易贴上标签。晚上,
爹偶尔会带一两个村里的男人回家喝酒。他们围着桌子,就着一碟咸菜花生米,
也能喝得面红耳赤。酒酣耳热时,那些平日里还算收敛的话,便毫无顾忌地冒了出来。
“要我说,根生,你也别太死心眼。女人嘛,跟谁不是过日子?跑了就跑了,再找一个就是!
”“就是!凭你的力气,还怕找不到婆娘?大不了……像老光棍那样,花钱买一个呗!
虽然贵点,但听话!”“买啥买?现成的不就有……”有人醉醺醺地,
目光意有所指地瞟向我睡觉的里屋,话没说完,就被旁边的人用胳膊肘捅了一下。
爹猛地灌了一口酒,呛得剧烈咳嗽起来,脸憋得通红,不知道是酒呛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他重重地把酒杯顿在桌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喝酒就喝酒,少他妈放屁!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油灯芯偶尔爆开的噼啪声。那种安静,比吵闹更让人窒息。
我蜷在里屋的炕上,用被子蒙住头,浑身冰冷。那个未尽的话头,
像一把悬在头顶的、生锈的钝刀,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来,只知道它一定会落。
这些看似零碎的、充满“关怀”或“玩笑”的话语,像无数条隐形的丝线,
在我周围编织成一张无形的大网。网的中心,就是我。而我那瘸了的腿,
阿妈“跟人跑了”的污名,都成了这张网更加牢固的理由。
他们似乎在用一种心照不宣的方式,
一步步地将我推向某个既定的、属于这山里许多女孩的、黑暗的归宿。阿妈的失踪,
仿佛只是一个开始,一个为我这个“多余”的丫头,腾出位置的信号。日子像村口那盘磨,
沉重而缓慢地转动着,碾碎着希望,也碾磨出生活粗糙的本来面目。
我开始更清晰地听懂那些盘旋在头顶的话,它们不再只是难听的噪音,
而是带着冰冷钩刺的网,一点点收紧。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往下熬,像钝刀子割肉。
直到那天下午,几辆呼啸而来的警车,再次打破了村子令人窒息的宁静。
他们直接开到了后山脚下。穿着统一服装的人越来越多,拉起了长长的黄色警戒线。
铁锹和锄头起落,泥土被一铲一铲地挖出来,堆成小山。全村的人都围了过去,踮着脚,
伸长了脖子,像一群被无形之手提着的鸭子。我和一群半大的孩子挤在最外围,
透过大人们腿脚的缝隙,能看到里面忙碌的身影,和越挖越深的土坑。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慌,像湿冷的雾气,在人群里弥漫开来。没人再大声议论,
只有压得极低的耳语和粗重的呼吸声。然后,不知是谁先惊叫了一声。紧接着,
像是瘟疫传染,恐慌炸开了。一具,两具,三具……警察们从那个越来越深的土坑里,
抬出来一具又一具东西,用白色的袋子装着,拉链严严实实地拉着。可那形状,分明就是人。
第七个袋子被抬上来时,有个警察脚下一滑,袋子重重地磕了一下,拉链崩开了一角,
一截已经完全白骨化的小腿掉了出来,在惨白的阳光下,晃得人眼睛刺痛。更刺眼的,
是那截白骨脚踝上,系着的一圈褪了色,但依旧能辨认出是红色的绳结。那编织的手法,
那打结的方式……我死死地攥紧了拳头,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的嫩肉里。我认得。
那是阿妈才会编的平安结。她说过,红绳辟邪,保平安。我的手腕上,曾经也系过一根,
后来旧了,断了,她就给我换了新的。她说,要一直戴着,菩萨会保佑我。现在,
这些保佑过我的,一模一样的红绳,系在了后山挖出来的,第七具女尸的脚踝上。
人群彻底乱了。哭喊声,咒骂声,呕吐声,还有警察厉声维持秩序的声音,混杂在一起。
“是秀英!那绳结是根生家秀英编的!”“天杀的!原来不是跟人跑了!是遭了毒手了!
”“是谁干的?!挖出来七……七个啊!”爹的脸色,在那一瞬间,
变得比地上的死人骨头还要惨白。他踉跄着后退,撞在身后的人身上,嘴唇哆嗦着,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有人扶住了他,他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那人的胳膊,
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喉咙发紧。阿妈……不是跑了?
她被人害了?和另外六个女人一起,被埋在了后山?是谁?混乱中,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推搡着回到家的。院子里空荡荡的,爹被警察留下来问话了。堂屋里,
还残留着摔碎的酒瓶渣子。后山的尸体被发现后,最初的震惊过去,
村里弥漫开一种更古怪的气氛。恐惧是真的,
但另一种更隐晦的情绪也在发酵——那是对“规矩”被打破的恼怒,
是对可能引火烧身的惶惶,还有一种……对“不守规矩”女人的、变本加厉的鄙夷。
“七个啊……作孽哦!” 王婆在井边捶打着衣裳,力道大得像在泄愤,“可话说回来,
那些女人要是不整天想着往外跑,能招来这祸事?安安分分待在屋里,相夫教子,
哪来这么多是非!”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媳妇,
怯生生地插了句嘴:“可她们…也可能是被…”“被什么被?!”王婆猛地打断她,
浑浊的眼睛一瞪,“一个巴掌拍不响!好端端的,人家怎么就盯上她们?还不是自己不安分!
你看我们这些老老实实过日子的,谁出过事?”那年轻媳妇立刻噤声,低下头用力搓洗衣裳,
不敢再言。我蹲在旁边洗几个瘦小的土豆,听着这话,心里像有寒冰在凝结。
她们的语气那么理所当然,仿佛那些被埋在后山的女人,她们的死,
首要的原因是她们自己的“不安分”。这种逻辑,比赤裸裸的恶意更让人胆寒。后来,
李婶来我家的次数更多了。她不再只是送吃的,开始帮我爹收拾屋子,
嘴里絮絮叨叨:“根生兄弟,你看这日子,总得过下去。丫头大了,总不能一直这么拖着。
我娘家那边有个远房亲戚,在铁山坳,家里条件还行,就是儿子…小时候发烧,
脑子不太灵光,但人老实,知道疼人。他们不挑,
就想要个能过日子、能生养的……”我爹依旧沉默,但抽烟的频率慢了下来,
像是在认真权衡。李婶趁热打铁:“彩礼他们愿意出这个数。”她伸出几个手指,
在我爹眼前晃了晃,“丫头过去,也算有个着落,总比留在家里,将来……你知道的,
名声也不好听。”“名声”……这两个字像两座山,压垮了多少山里的女人。阿妈“死了”,
所以她的女儿也带着“原罪”,需要被尽快、尽量不亏本地“处理”掉。
就连村里那些半大的小子,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他们不再只是无视,有时会聚在一起,
对着我指指点点,发出哄笑。有一次,我瘸着腿背柴禾走过,一个半大小子故意伸脚绊我,
我摔在地上,柴禾散了一地。他们围着我笑:“瘸子还想学人跑?”“跟她阿妈一个德性!
”“以后肯定也是个便宜货!”我趴在地上,泥土的气息混着眼泪的咸涩钻进鼻腔。那一刻,
我清晰地感觉到,这个村子,从垂暮的老人到懵懂的孩童,
同一种毒素——一种视女性为物件、为附属、为可以随意评判、交易甚至摧毁的存在的观念。
阿妈的死,非但没有换来悔悟,反而成了加固这观念的又一块基石。恐惧和绝望像野草,
在我心里疯狂滋长,然后,在那封血书冰冷的熨烫下,
慢慢凝结成一种坚硬的、带着棱角的东西。报复的念头,不再是冲动,
而成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李婶藏银镯子的灶台砖缝,我知道。
村会计晚上常偷偷去邻村找那个暗娼,我知道。王婆总吹嘘她儿子在外面挣大钱,
其实是在城里给人当打手,专干些见不得光的勾当,我也知道。
还有那个总用猥琐目光打量我的老光棍,
他屋里藏着几件明显不属于他的、花色鲜艳的女人内衣……这些零碎的、肮脏的秘密,
像散落在地上的毒蘑菇。以前我只觉得恶心,现在,我知道它们有用。警察还在调查,
但进展缓慢。村民们开始统一口径,对外来的警察充满了不信任和隐隐的敌意。
他们像一块被水浸透的厚木板,难以撬动。那就从内部烧穿它。我选择了一个时机。那天,
爹又被叫去问话,李婶大概是做贼心虚,在家里指桑骂槐地哭闹,说有人污蔑她。
村里人心浮动。夜里,我像个幽灵一样溜出家门。月光很亮,照得我脸色惨白。
我没有去后山,而是先去了李婶家。我不仅把一根红绳系在她家门环上,
还用从灶台抠下来的、混合着泥土的黑灰,
在她家门板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类似银镯子的圆圈。接着,是村会计家。
我把红绳系在他家窗棂最显眼的位置,然后,
将一张早就准备好的、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模糊的男女依偎的图片,塞进了他家的门缝。
王婆家……老光棍家……我像一个沉默的播种者,在寂静的夜色里,
精准地在每一块孕育着罪恶的土地上,埋下恐慌的种子。我用的不是直接的指控,而是暗示,
是联想,是勾起他们内心最恐惧场景的碎片。红绳,是阿妈的标记,
也是所有参与者共同的噩梦。而附加的那些“小礼物”,则是直指他们个人秘密的利刃。
做完这一切时,天还没亮。我回到家里,躺在冰冷的炕上,心跳如鼓,却异常平静。第二天,
恐慌以比上一次更猛烈、更精准的态势爆发了。李婶看到门上的镯子印记,当场晕了过去。
村会计捡起那张图片,脸瞬间煞白,手抖得几乎拿不住东西。王婆对着自家门上的红绳,
不再是尖叫,而是发出一种像被掐住脖子的、绝望的呜咽。老光棍则像见了鬼一样,
把自己锁在屋里,一整天没敢出门。这一次,恐慌不再仅仅是针对“鬼魂索命”,
更是针对“秘密被窥破”的极致恐惧。他们开始疯狂地互相猜忌,是谁出卖了谁?
那个系红绳的“鬼”,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怀疑的链条一旦开始崩解,速度是惊人的。
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为了自保,有人开始向警察吐露“别人的”秘密,试图将祸水引开。
一根又一根肮脏的线头,就这样被扯了出来。警察的调查,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当手铐再次亮出,戴在爹、李婶、村会计、王婆儿子以及老光棍手腕上时,
他们脸上除了恐惧,还有一种被彻底看穿、无力回天的灰败。爹在被押上警车前,
最后一次回头看我。我站在人群边缘,依旧瘸着腿,脸上是符合年龄的茫然和无措。
只有他自己能看到,我看着他,嘴角极其轻微地、几乎不被察觉地,向上弯了一下。
那不是一个孩子的笑容,那里面淬着冰,带着血,和一丝属于猎手的、残酷的怜悯。
他看着我的眼神,从怨毒,变成了彻底的、如同见到怪物般的骇然。警车呼啸着远去,
带走了笼罩村庄多年的部分阴影,也带走了我作为“受害者女儿”的短暂身份。我站在原地,
阳光刺眼。脚踝上,阿妈留下的那根旧红绳,早已被我取下,妥善收藏。新的红绳,
我已经会编了。编得和阿妈一样好。而这,仅仅是个开始。铁山坳,
还有更多像这里一样的山村,它们需要被“清理”。用我的方式。铁山坳的夜,
比我的故乡更沉,更死寂。这里的山仿佛离天更近,压得人喘不过气。我被卖到了张家。
张老蔫和他婆娘,像两尊被风干了的泥塑,脸上刻着同样的麻木和算计。他们的傻儿子,
叫铁锁,二十多岁的年纪,智力却像个五六岁的孩子,整天咧着嘴流口水,
看到我就“媳妇、媳妇”地叫,伸手要来抓我。我故技重施,将怯懦和顺从演到了骨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