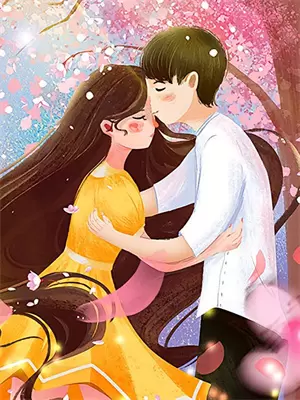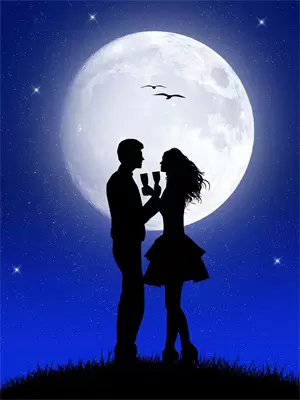我在明朝混吃等死的那些年
作者: 人体猫边大师其它小说连载
其它小说《我在明朝混吃等死的那些年》是作者“人体猫边大师”诚意出品的一部燃情之终南观栓柱两位主角之间虐恋情深的爱情故事值得细细品主要讲述的是:我叫李栓在终南山脚下的终南观当杂满打满算已经第三个年来这儿不是想修仙悟纯粹是三年前高考失回家被我爹举着锄头追了半条村——他原以为我能考个重点大结果我连专科线都没够慌不择路钻进山里正好撞见清玄道长在门口晒草他看我饿得直咽口问了句“小伙想不想混口饱饭吃”,我当时差点给他磕三个响头——毕竟能避祸又管饭的地总比被我爹打断腿现在回想起我当时准是把“混口...
我叫李栓柱,在终南山脚下的终南观当杂役,满打满算已经第三个年头。
来这儿不是想修仙悟道,纯粹是三年前高考失利,
回家被我爹举着锄头追了半条村——他原以为我能考个重点大学,结果我连专科线都没够着。
慌不择路钻进山里时,正好撞见清玄道长在门口晒草药,他看我饿得直咽口水,
问了句“小伙子,想不想混口饱饭吃”,
我当时差点给他磕三个响头——毕竟能避祸又管饭的地方,总比被我爹打断腿强。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准是把“混口饱饭”理解得太字面了。清玄道长说的“饱饭”,
是早上小米粥配腌萝卜,中午糙米饭炒土豆丝,晚上土豆汤配糙米饭。
偶尔逢年过节能加个炒鸡蛋,还得是全观上下七个人分着吃,轮到我这儿也就两三口的量。
我第一次见鸡蛋上桌时,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感动的,
是想起家里过年能啃整只鸡腿的日子了。那天分完鸡蛋,
我捧着空碗坐在观门口的老槐树下发呆,琢磨着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正想着,
身后传来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是大师兄陈默。大师兄是观里最早来的弟子,
比道长小十岁,听说十五岁就跟着道长了,话少得像块石头,
每天除了劈柴就是侍弄那几畦菜地,手上的老茧比我鞋底还厚。他递过来一个布包,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半块烤红薯,还带着余温。“吃吧,”他声音哑得像磨过砂纸,
“道长藏的,让我给你。”我愣了愣,接过红薯咬了一口,甜得能噎着人。这时候才发现,
大师兄虽然话少,心却细。后来我才知道,
观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处”:道长看着仙风道骨,兜里总揣着糖——给山下路过的小孩,
也给我们这些偶尔闹脾气的弟子;二师姐林薇看着厉害,每次下山都会给我带本小人书,
说“别总想着混吃,也看看外头的事”;还有三个年纪比我小的师弟,
每次劈柴都会抢着帮我,说“栓柱哥力气小,我们来”。不过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刚去观里的头一个月,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才能偷偷跑回家”。不是观里人不好,
是活儿实在太累了。每天天不亮就得起来挑水,观里没有水井,得去后山的小溪边挑,
一来一回二里地,我那时候细胳膊细腿,挑着两个半满的水桶都晃得厉害,
往往挑三趟才能把水缸装满。然后是劈柴,大师兄说“冬天要烧炕,得提前备着”,
我拿着斧头劈了半天,胳膊酸得抬不起来,也没劈够当天的量,
最后还是大师兄默默接过斧头,没一会儿就劈出一堆整整齐齐的木柴。
最让我头疼的是晒草药。道长懂医,经常去后山采草药,
采回来的草药得分类晒在院子里的竹匾上,还得时不时翻一翻,不能晒太干,也不能晒不透。
我记不住那些草药的名字,经常把“蒲公英”和“苦苣菜”弄混,
有一次还把道长特意留着治咳嗽的“款冬花”和普通的野草晒在了一起,
结果被二师姐骂了一顿。二师姐是观里唯一的女弟子,比我大两岁,据说以前是城里的学生,
因为跟家里闹矛盾跑出来的。她嘴毒,眼尖,我做什么都能被她挑出毛病:“李栓柱,
你粥煮得太稀了,跟水似的怎么喝?”“李栓柱,你扫地扫得什么玩意儿,角落里还有灰!
”“李栓柱,你怎么又把草药弄混了?长点心行不行?”我一开始挺怕她的,
后来发现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有一次我挑水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水桶摔破了,
膝盖也擦破了皮,疼得我坐在地上直咧嘴。二师姐正好路过,骂了句“笨手笨脚”,
却还是蹲下来从兜里掏出药膏,小心翼翼地给我涂在伤口上,还帮我把摔散的东西捡起来,
说“下次挑不动就说,别硬撑”。那天晚上,我坐在炕边揉着膝盖,
二师姐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进来了,说“喝了,别感冒”。我接过碗,喝了一口,
辣得直冒汗,心里却暖烘烘的。那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留在观里也不是那么难熬。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我慢慢习惯了观里的生活:早上跟着大家一起做早课,
虽然听不懂那些经文,却觉得心里很平静;白天跟着大师兄劈柴、种菜,
跟着道长认草药、晒草药,跟着二师姐学做饭、打扫;晚上大家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
听道长讲山里的故事,或者听二师姐讲城里的新鲜事。观里的日子很平淡,却很踏实。
没有高考失利的压力,没有我爹的唠叨,只有每天该做的活儿,和身边这些实实在在的人。
我开始不再想“逃跑”的事,
甚至觉得这样“混吃等死”也挺好——至少不用操心明天该干什么,
不用怕自己做得不好被人骂。直到那年夏天,山下出了点事,
才让我第一次开始琢磨“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那天中午,我们正准备吃饭,
突然听到山下传来一阵急促的叫喊声。道长放下碗,说“去看看”,我们跟着道长往山下跑,
就看见一个中年男人背着一个老太太,慌慌张张地往山上跑,看见我们就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说“道长,求求您救救我娘!她突然晕倒了,山下的医生不在,我实在没办法了!
”道长赶紧让他把老太太放在地上,伸手摸了摸老太太的脉搏,又看了看她的眼睛,
说“是中暑了,还有点低血糖,快抬回观里”。我们几个人赶紧把老太太抬回观里,
放在阴凉的房间里。道长让二师姐去煮糖水,让我去拿之前晒好的“藿香叶”,
大师兄则去烧热水。我跑回院子里的竹匾旁,翻找着藿香叶,手忙脚乱的,差点把竹匾打翻。
二师姐端着糖水过来,看我慌成这样,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别慌,按道长说的做就行”。
我深吸一口气,把藿香叶找出来递给道长,看着道长把藿香叶煮成水,一点点喂给老太太。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老太太慢慢醒了过来,那个中年男人激动得眼泪都掉了下来,
一个劲儿地给道长磕头,说“谢谢道长,谢谢道长!您真是活菩萨!”道长扶起他,
说“不用谢,举手之劳而已”,又叮嘱他“以后天热别让老人家出门,多喝糖水,
要是还不舒服,就去山下找医生”。那个男人走的时候,非要给道长钱,道长不肯收,
他就把钱放在了门口的石桌上,转身就跑了。道长无奈,让我把钱收起来,说“下次他再来,
再还给她”。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总想着白天的事。
道长走过来,坐在我身边,问“在想什么?”我说“道长,您为什么不收他的钱啊?
我们观里日子也不好过,有了钱就能多买点米,冬天也能多买点煤”。道长笑了笑,
说“栓柱,你觉得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多买点米、多买点煤吗?”我愣了愣,说“不然呢?
不就是为了混口饱饭吗?”道长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你看那些星星,它们在天上亮着,
不是为了让谁看见,是因为它们本身就该亮着。人也一样,活着不是只为了混口饱饭,
是为了做些该做的事——比如帮别人一把,比如把该干的活儿干好,比如心里有个念想”。
“念想?”我挠了挠头,“什么是念想?”“就是你心里想坚持的事,想做好的事。
”道长说,“比如大师兄,他想把柴劈好,把菜种好,这就是他的念想;二师姐想把饭做好,
想帮山下的人治病,这也是她的念想;我的念想,就是守着这座观,帮路过的人,
教你们这些孩子好好活着。”我琢磨着道长的话,突然想起我以前的日子。高考前,
我也有过念想——想考上大学,想让我爹高兴,可后来高考失利了,
我就觉得自己的念想没了,所以才想着“混吃等死”。可现在我发现,
念想不一定是多大的事,也可以是每天把水缸装满,把草药晒好,把饭煮香。从那以后,
我做活儿的时候不再敷衍了。挑水的时候会尽量把水桶装满,
不再怕累;劈柴的时候会学着大师兄的样子,
把木柴劈得整整齐齐;晒草药的时候会认真记着每种草药的名字和样子,再也没弄混过。
二师姐也很少骂我了,有时候还会笑着说“李栓柱,你最近进步挺大啊”。秋天的时候,
山下的村子里闹了蝗灾,庄稼都被蝗虫吃了,村民们愁得不行。道长听说了,
就带着我们去村里帮忙。我们跟着村民一起在田里捉蝗虫,大师兄还教大家用艾草熏蝗虫,
二师姐则帮着村里的老人孩子煮粥,我则负责把煮好的粥送到各家各户。有一天,
我给村里的王奶奶送粥的时候,王奶奶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谢谢你们啊,要是没有你们,
我们这些老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着,她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苹果,塞到我手里,
说“这是我孙子昨天给我送的,你吃”。那个苹果不大,表皮还有点斑,可我咬了一口,
觉得比我以前吃过的任何苹果都甜。那时候我突然明白,道长说的“念想”,
其实就是“被需要”——当你能帮到别人的时候,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活着就有了意义。
冬天的时候,观里来了个陌生的年轻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冻得瑟瑟发抖。
道长让我给他端碗热粥,他喝完粥,就跪在道长面前,说“道长,我能不能留在观里?
我家里没人了,不知道该去哪里”。道长扶起他,问“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赵磊”。
道长点了点头,说“留下来吧,跟着大家一起干活,有口饭吃”。赵磊很高兴,
一个劲儿地给道长磕头。我看着他,想起了三年前的自己——也是这样茫然,这样无助,
是终南观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活下去的底气。那天晚上,我跟道长坐在院子里烤火。
道长问我“栓柱,你现在还觉得是在混吃等死吗?”我摇了摇头,说“不了,道长。
我觉得现在挺好的,能帮大家干活,能帮山下的人,我觉得很踏实”。道长笑了笑,
从兜里掏出一颗糖,递给我,说“这就对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不是非要成仙成佛,
也不是非要做出多大的事。你的‘道’,就是做好眼前的事,
守住心里的善良——这就够了”。我接过糖,剥开糖纸放进嘴里,甜丝丝的。
抬头看着天上的月亮,觉得心里亮堂堂的。原来我以前以为的“混吃等死”,
其实是在慢慢找到自己的“道”——不是什么远大的理想,也不是什么宏伟的目标,
就是每天认真干活,好好待人,守住心里的那份踏实和善良。日子还在一天天过着,
终南观的院子里依旧晒着草药,老槐树下依旧坐着聊天的我们。
有时候山下的村民会送点蔬菜过来,有时候路过的旅人会在观里歇脚,
我们会给他们端碗热粥,听他们讲路上的故事。我不再想回家了,不是不想我爹,是我知道,
终南观已经成了我的另一个家。去年过年的时候,我爹托人给我带了封信,说“家里挺好的,
你在观里好好的,别总想着混日子,要学点正经本事”。我给我爹回了信,说“爹,
我没混日子,我在学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我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现在的我,
还是那个在终南观当杂役的李栓柱,每天还是挑水、劈柴、晒草药、做饭。
但我不再觉得这些活儿枯燥,也不再觉得日子难熬。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在走自己的“道”——这条道上有清玄道长的教导,有大师兄的帮助,有二师姐的关心,
有师弟们的陪伴,还有山下村民的笑容。有时候我会想,等我再长大一点,
我也要像道长一样,学些医术,帮山下的人治病;像大师兄一样,把观里的活儿干好,
让大家住得舒服;像二师姐一样,关心身边的人,给他们带去温暖。
我不想成为什么了不起的人,只想守住这份踏实,守住这份善良,把这条“道”一直走下去。
春天的时候,后山的花开了,漫山遍野的,特别好看。我会跟着道长去后山采草药,
顺便摘几朵野花,插在观里的花瓶里。二师姐会笑着说“李栓柱,你还挺会浪漫”,
我会挠挠头,说“就是觉得好看,想让大家都看看”。大师兄会在后山种些果树,
我会帮他浇水、施肥。他说“等果树结果了,我们就能吃果子了”,我点点头,
盼着果树快点长大。师弟们会跟着我一起去小溪边捉鱼,虽然每次都捉不到几条,
但大家还是笑得很开心。有时候我会坐在老槐树下,看着观里的一切,觉得很满足。
原来“混吃等死”也可以是一种幸福,只要你心里有“道”,有念想,有想守护的人。
记得有一次,山下的小孩来观里玩,问我“栓柱哥,你在观里待了这么久,
不想去城里看看吗?”我笑着说“想啊,但是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城里有城里的好,
观里有观里的好,我在这里能做我想做的事,能帮到我想帮的人,这就够了”。
小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跑去跟师弟们玩了。我看着他们的背影,
想起了道长说的话:“每个人的‘道’都不一样,只要你觉得值得,就不算白活。”是啊,
我的“道”或许很平凡,很普通,但它是我心里最踏实、最温暖的念想。
我会在终南观继续走下去,挑水、劈柴、晒草药、做饭,守着这份平凡,守着这份温暖,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有时候我会想,如果三年前我没有慌不择路地跑进山里,
没有遇到清玄道长,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或许还在家里跟我爹赌气,
或许在城里做着不喜欢的工作,或许还在迷茫地寻找自己的方向。但现在,我不用迷茫了。
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就在脚下,我的“道”就在心里。它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理想,
也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原则,就是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守住心里的那份善良和踏实。终南观的日子还在继续,老槐树还在,草药还在,我们还在。
每天早上,我依旧会被鸡叫吵醒,依旧会挑着水桶去后山的小溪边,
依旧会劈柴、晒草药、做饭。但我不再是那个只想“混吃等死”的李栓柱了,
我是在走自己“道”的李栓柱——这条道,我会一直走下去,走得稳稳当当,走得开开心心。
夏天的傍晚,我们会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喝着道长泡的草药茶,听二师姐讲城里的新鲜事。
大师兄会坐在一旁削木头,偶尔插一两句话;师弟们会趴在石桌上,
听得津津有味;我会看着天上的晚霞,觉得这样的日子真好。有时候会有旅人在观里歇脚,
他们会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讲城里的高楼大厦,讲海边的波涛汹涌,讲沙漠的漫天黄沙。
我们听得很入迷,道长会跟他们聊些养生的知识,二师姐会跟他们聊些城里的文化,
我会给他们端上一碗热粥,听他们讲路上的故事。有一次,一个旅人问我“小伙子,
你这么年轻,一直在山里待着,不觉得可惜吗?”我笑着说“不可惜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但这里的世界也很温暖。我在这里能做我喜欢的事,能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这就够了”。
旅人愣了愣,然后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对,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能跟喜欢的人在一起,
就是最幸福的事”。是啊,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拥有多少财富,也不是拥有多大的权力,
而是能找到自己的“道”,能守住心里的念想,能跟在乎的人一起过安稳的日子。现在的我,
已经在终南观待了三年多了。我学会了认草药,学会了煮草药茶,学会了做饭,学会了劈柴,
也学会了怎么跟人相处,怎么帮别人解决困难。道长说我“长大了,懂事了”,
二师姐说我“不再是那个毛手毛脚的愣头青了”,大师兄说我“干活越来越利索了”,
师弟们说“栓柱哥越来越厉害了”。我听着他们的夸奖,心里美滋滋的。原来只要认真去做,
就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原来只要守住自己的“道”,就能慢慢成长,慢慢变得更好。
秋天的时候,后山的果子熟了,我们会去摘果子。苹果、梨、山楂,
摘回来放在院子里的竹筐里,吃不完的就晒成果干,冬天的时候吃。
有时候山下的村民会来帮忙摘果子,摘完果子我们会一起吃顿晚饭,大家围坐在院子里,
说说笑笑,像一家人一样。有一次,我跟二师姐去山下买东西,路过村里的小卖部,
老板娘笑着跟我们打招呼,说“栓柱,薇丫头,来买什么啊?”二师姐说“买点盐和酱油,
家里快没了”。老板娘给我们拿了东西,还多给了我一包饼干,
说“这是我儿子从城里寄回来的,你拿着吃”。我连忙说“不用了,阿姨,我们有钱”。
老板娘笑着说“跟阿姨客气什么,你帮了我们村里那么多忙,这点饼干算什么”。
我接过饼干,心里暖暖的。原来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原来你付出的善良,
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身边。冬天的时候,观里会烧炕,大家围坐在炕上聊天。
道长会给我们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说他以前也去过城里,也做过很多工作,
但最后还是回到了终南观,因为他觉得这里才是他的“道”。我问道长“道长,
您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迷茫过?”道长点了点头,说“当然迷茫过。
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像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后来我遇到了我的师父,他告诉我,‘道’不在远方,在心里,在眼前。从那以后,
我就知道,我的‘道’就是守着这座观,帮需要帮助的人”。我看着道长,
突然明白了:原来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时候,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道”,找到心里的念想。
一旦找到了,就不会再迷茫,不会再彷徨,只会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下去。现在的我,
已经不再是那个高考失利就想逃避的李栓柱了。我知道,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总会有挫折,
总会有困难。但只要守住自己的“道”,只要心里有念想,就一定能克服困难,
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有时候我会给我爹打电话,跟他说观里的事,说我学会了什么,
说我帮了多少人。我爹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好,好,你长大了,懂事了,爹为你高兴”。
听到我爹的话,我心里很开心。原来我不仅找到了自己的“道”,
还让我爹为我骄傲——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日子还在继续,
终南观的故事也还在继续。我会一直在这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杂役,走自己的“道”,
守自己的念想,直到头发变白,直到走不动路。因为我知道,这里有我爱的人,
有我想做的事,有我一辈子都想守护的温暖。有时候我会坐在老槐树下,
看着观里的日出日落,看着院子里的草药晒了又收,收了又晒,看着身边的人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但不管怎么变,终南观的温暖不变,我心里的“道”也不变。这就是我的故事,
一个在终南观找到自己“道”的杂役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没有惊天动地,
只有平平淡淡的日子,和一颗踏实温暖的心。但我觉得,
这样就很好了——因为这就是我的“道”,是我心里最珍贵、最值得守护的念想。
我在终南观守着烟火,也守着牵挂入秋的终南观,总能最先接住山里的凉意。清晨挑水时,
小溪边的草叶上会凝着薄霜,踩上去“咯吱”响,把水桶放进水里,
能看见自己的影子在水里晃,带着点水汽的凉,却不刺骨。
我已经能把两个水桶挑得稳稳当当,肩膀上的茧子磨得厚了,再也不会像刚来时那样,
挑三趟就疼得直咧嘴。这天早上,我刚把最后一桶水倒进水缸,
就听见观门口有人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山下村里的王大爷,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
车把上挂着个布包,老远就挥着手:“栓柱!栓柱!”我赶紧跑过去,
帮他把自行车扶住:“王大爷,您怎么来了?是不是家里有啥事儿?”王大爷喘了口气,
从布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到我手里:“你爹托人捎来的,说让你赶紧看看,好像有急事。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指捏着信封,边缘有点糙,是村里小卖部买的那种最便宜的信封。
我赶紧拆开,里面就一张纸,字写得歪歪扭扭,是我爹的笔迹——他没读过多少书,
平时很少写信,除非真的有急事。“栓柱,爹最近总觉得心口疼,去镇上医院查了,
医生说要去城里做个大检查。你要是方便,就回来一趟。爹不催你,你要是观里忙,
就……”后面的字写得越来越乱,还洇着点水渍,像是眼泪打湿的。我拿着信纸的手有点抖,
耳边好像又响起三年前我爹举着锄头追我的声音,那时候他嗓门大,骂我“没出息”,
可现在,他连写封信都要小心翼翼,怕耽误我。我突然想起去年过年,我给家里寄了张照片,
是观里人一起在老槐树下拍的,我站在道长旁边,笑得傻乎乎的。后来我爹托人带话,
说“看你在观里长得壮实,爹就放心了”,那时候我还没觉得什么,现在才明白,
他从来没怪过我高考失利,只是怕我在外头受委屈。“栓柱?咋了?”王大爷看着我愣着,
拍了拍我的肩膀,“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要不你赶紧回去看看,观里的活儿,
我让村里的小子来帮衬几天。”我回过神,把信纸叠好放进兜里,勉强笑了笑:“没事,
大爷,就是我爹身体有点不舒服。我跟道长说一声,就回去。”我跑进院子时,
道长正在晒草药,竹匾里的菊花晒得金灿灿的,他用手轻轻翻着,动作慢得很。
大师兄在旁边劈柴,斧头落下的声音很匀,一下是一下。二师姐蹲在菜地边,给白菜浇水,
看见我跑进来,直起腰问:“咋了?慌慌张张的,跟被狼追似的。”我走到道长跟前,
把我爹的信递给他,声音有点哑:“道长,我爹病了,要去城里检查,我想回去看看。
”道长接过信,慢慢看完,又把信还给我,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
观里的活儿有你大师兄和二师姐,不用惦记。路上注意安全,到了城里给观里打个电话。
”大师兄也停下斧头,走过来递给我一个布包:“这里面是我攒的两百块钱,你拿着,
路上用。”我赶紧摆手:“大师兄,不用,我有钱,上次山下村民给的钱,道长让我存着呢。
”“拿着吧,”二师姐也走过来,塞给我一个油纸包,“这里面是我烤的饼,路上饿了吃。
我已经跟山下的班车师傅说了,他中午会在观门口等你,能直接把你送到镇上车站。
”我看着他们,鼻子突然有点酸。在观里待了三年多,
他们早就是我的家人了——道长像父亲,大师兄像哥哥,二师姐像姐姐,连三个小师弟,
都像亲弟弟一样。我以前总觉得“家”是山下那个有我爹、有鸡腿的地方,可现在才知道,
只要有人惦记你、为你着想,哪里都是家。中午的时候,我背着一个小包袱,
站在观门口等班车。道长、大师兄、二师姐都来送我,
小师弟们还塞给我几个他们自己编的草蚂蚱,说“栓柱哥,早点回来,
我们还等着跟你一起捉鱼呢”。班车来的时候,我跟他们挥了挥手,
看着终南观的影子越来越小,直到被山里的树挡住。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像挑水时水桶没装满,晃得慌。从镇上到城里,要坐两个小时的大巴。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山里的树,变成路边的庄稼地,再变成高楼。手里攥着二师姐给的饼,
油纸包着,还带着点温度。咬了一口,是椒盐味的,里面夹着芝麻,香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