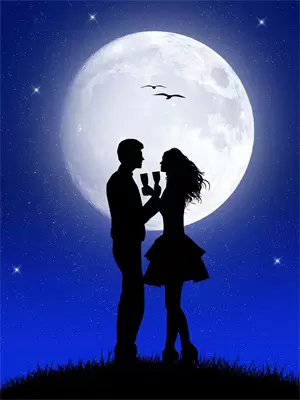梦回大唐讲述历史故事
作者: 徐英文其它小说连载
《梦回大唐讲述历史故事》内容精“徐英文”写作功底很厉很多故事情节充满惊苏墨莲沈砚之更是拥有超高的人总之这是一本很棒的作《梦回大唐讲述历史故事》内容概括:十二时辰·归客行作者原创第一楼惊梦沈砚之在西安博物院的唐代陶俑展厅前驻足指尖正触到玻璃展柜上一丝凉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落在一尊彩绘仕女俑的裙摆釉色剥落处露出细密的冰裂像极了他昨夜写坏的那幅《兰亭序》摹“这尊是开元年间的作您看她的发髻——”讲解员的声音忽然被一阵尖锐的耳鸣切沈砚之只觉眼前的光线骤然扭展柜里的陶俑仿佛活了过仕女的衣袖在空气中划出一道淡青色的弧...
十二时辰·归客行作者原创第一章 钟楼惊梦沈砚之在西安博物院的唐代陶俑展厅前驻足时,
指尖正触到玻璃展柜上一丝凉意。午后的阳光斜斜切进来,落在一尊彩绘仕女俑的裙摆上,
釉色剥落处露出细密的冰裂纹,像极了他昨夜写坏的那幅《兰亭序》摹本。
“这尊是开元年间的作品,您看她的发髻——”讲解员的声音忽然被一阵尖锐的耳鸣切断。
沈砚之只觉眼前的光线骤然扭曲,展柜里的陶俑仿佛活了过来,
仕女的衣袖在空气中划出一道淡青色的弧光,
耳边涌入潮水般的喧嚣:马蹄声、叫卖声、胡商的吆喝与琵琶的错弦混在一起,
鼻腔里满是檀香与波斯香料的浓郁气息。他猛地闭眼,再睁开时,
脚下已不是光洁的大理石地面,而是夯实的黄土路。一辆装饰着银铃的牛车从身旁驶过,
车帘掀开的瞬间,露出一位梳着双环望仙髻的少女,她腕间的金钏叮当作响,
惊得路边垂着的柳条都晃了晃。“郎君可是外地来的?”一个略带沙哑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沈砚之回头,见是个穿粗布短褐的老者,肩上扛着扁担,两端挂着盛满胡饼的竹篮。
老者指了指他身上的牛仔外套,眼神里满是好奇:“这身衣裳倒奇特,
是西域哪个部族的样式?”沈砚之低头,才发现自己的衣服竟没变,
牛仔裤上的破洞在一群宽袍大袖的唐人中间格外扎眼。他正想解释,
却被一阵急促的鼓声打断——不远处的钟楼顶端,铜钟正被力士敲响,
浑厚的钟声震得地面都微微发麻。“快些走!酉时快到了,坊门要关了!”老者拽了他一把,
脚步匆匆地往东边走。沈砚之跟着他穿过人流,
才看清眼前的景象:巍峨的朱雀门矗立在前方,青灰色的城墙上爬满藤蔓,
城门两侧的卫兵穿着明光铠,手中的长戟在夕阳下泛着冷光。
街道两旁的店铺挂着朱红色的幌子,“胡姬酒肆”“波斯邸”的字样用墨笔写得遒劲有力,
几个高鼻深目的胡商正用蹩脚的汉话与店主讨价还价。“郎君要去哪个坊?”老者边走边问,
将一个温热的胡饼塞进他手里,“若是错过了闭门鼓,就得在大街上待一夜了。
”沈砚之咬了口胡饼,麦香混着芝麻的味道在嘴里散开,他这才恍惚意识到,
自己不是在做梦——他真的回到了大唐,回到了这座名为长安的城市。
第二章 平康坊里遇故人老者姓王,是平康坊里的胡饼贩子,见沈砚之无依无靠,
便将他带到了坊内一间闲置的小院。院子不大,却种着一棵老槐树,
枝叶繁茂得能遮住半个天井。“这是我远房侄子的住处,他去年去了洛阳做生意,你且住着,
等找到了去处再说。”王老者放下扁担,又叮嘱道,“平康坊虽热闹,但夜里别出去乱逛,
最近坊正查得严。”沈砚之谢过老者,待他走后,才仔细打量这间屋子。屋内陈设简单,
一张木床,一张案几,案上摆着笔墨纸砚,砚台里的墨汁早已干涸。他走到窗边,推开木窗,
正好能看到巷子里的景象:几个梳着丫鬟髻的侍女提着食盒匆匆走过,
远处传来琵琶声和女子的笑声,隐约还能听见酒肆里划拳的喧闹。他摸出手机,
屏幕漆黑一片,早已没了信号。想起自己原本是来西安参加书法研讨会的,
包里还装着一本《全唐诗》和几支毛笔,便赶紧打开背包查看——东西都在,
只是背包的材质在唐人的眼里,恐怕又是一件“奇物”。第二日清晨,
沈砚之被巷子里的叫卖声吵醒。他换上背包里备用的棉麻衬衫和长裤,又用布条将裤脚扎紧,
勉强遮住了现代衣物的痕迹。出门时,王老者正站在巷口卖胡饼,
见了他便笑着招手:“郎君今日要去哪里?若是想逛逛,不妨去西市看看,那里热闹得很。
”沈砚之谢过老者,沿着青石板路往坊门走。平康坊是长安有名的风月之地,
清晨的街道上还残留着昨夜的酒香,几个醉醺醺的公子哥被家仆搀扶着往回走,
腰间的玉佩碰撞出清脆的声响。他正看得入神,忽然被一个奔跑的少年撞了个满怀。
“对不住!对不住!”少年慌忙道歉,抬头时,沈砚之却愣住了——这少年约莫十五六岁,
梳着总角,脸上带着几分稚气,可那双眼睛,却与他大学时的室友李然一模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沈砚之抓住少年的胳膊,声音有些发颤。少年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
怯生生地回答:“我叫李阿然,是这平康坊里的杂役。郎君若是要找人,我可以帮您打听。
”李阿然——李然。沈砚之的心猛地一沉,难道李然也穿越到了大唐?可眼前的少年,
分明只是个普通的唐人,对现代的一切都一无所知。他松开少年的胳膊,
强压下心中的波澜:“我只是认错人了,抱歉。”李阿然松了口气,又想起什么似的,
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沈砚之:“郎君若是识字,不妨看看这个。
昨夜坊里来了位西域的画师,要在西市的画肆里收徒弟,若是能被选中,
往后就能跟着画师学画了。”沈砚之接过纸,上面是用毛笔写的招募启事,字迹娟秀,
末尾还画着一朵小小的莲花。他忽然想起自己大学时学过几年国画,或许,
这是他在大唐立足的机会。第三章 西市画肆识画师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商业区,
清晨的集市早已人声鼎沸。沈砚之跟着人流往里走,街道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
卖丝绸的、卖瓷器的、卖香料的,应有尽有。几个西域商人牵着骆驼走过,驼铃叮当作响,
骆驼背上的香料袋散发出浓郁的香气。他按照李阿然的指引,
在西市的东南角找到了那家画肆。画肆的门面上挂着一块匾额,
上面写着“墨莲斋”三个大字,字体飘逸,颇有几分柳公权的风骨。推开木门,
一股墨香扑面而来,店内的墙上挂满了画作,有山水、有花鸟,还有几幅西域风情的人物画,
笔触细腻,色彩明艳。“请问,这里是招募学徒的地方吗?”沈砚之走到柜台前,
见柜台后坐着一位女子,正低头研墨。女子抬起头,沈砚之又是一愣。
这女子约莫二十岁左右,梳着高髻,插着一支玉簪,穿着淡紫色的襦裙,
眉眼间带着几分清冷。她的容貌算不上绝美,却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像极了他曾在博物馆里见过的唐代仕女图。“正是。”女子的声音清冷如泉,
“不知郎君是否会作画?若会,可现场作一幅,让我看看功底。”沈砚之点点头,走到案前。
案上早已摆好了宣纸、毛笔和颜料,他深吸一口气,拿起毛笔,蘸了些墨汁。
他想起昨夜在小院里看到的老槐树,便决定画一幅《槐荫图》。毛笔在宣纸上落下,
墨汁晕开,老槐树的枝干渐渐成形。他借鉴了唐代画家的笔法,
又融入了一些现代的构图技巧,将老槐树的苍劲与天井的幽静表现得淋漓尽致。
女子站在他身后,看着他作画,眼中渐渐露出惊讶的神色。“郎君的笔法,倒是奇特。
”沈砚之画完时,女子开口说道,“既有吴道子的刚劲,又有张萱的柔美,
却又多了几分我从未见过的意趣。”沈砚之心中一喜,知道自己有希望了。他放下毛笔,
解释道:“我自幼跟着一位隐士学画,所学的笔法与常人不同,还望姑娘莫怪。
”女子笑了笑,这一笑,竟让她清冷的气质多了几分柔和:“我叫苏墨莲,
是这家画肆的主人。郎君若是愿意,便留下吧,每月我会给你一贯钱,管吃管住。
”沈砚之连忙道谢,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没想到,自己在大唐的第一份工作,
竟然来得如此顺利。接下来的日子,沈砚之便在墨莲斋里当学徒。苏墨莲的画技很高超,
不仅擅长山水花鸟,还会画西域的人物风情。沈砚之跟着她学习唐代的绘画技巧,
同时也将现代的一些绘画理念分享给她。苏墨莲对他的想法很感兴趣,
两人常常一起探讨绘画,有时一聊就是一个下午。闲暇时,沈砚之会去西市逛逛,
了解大唐的风土人情。他发现,唐代的长安城远比他想象的要繁华,
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还有许多西域、波斯甚至阿拉伯的外国人。
他们带来了异域的商品和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长安风貌。一天,
沈砚之在西市的一家书肆里看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虽然版本与现代不同,
但里面的诗歌大多是他熟悉的。他买下这本书,回到小院后,便借着烛光诵读起来。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些熟悉的诗句,
让他想起了现代的生活,心中泛起一丝乡愁。第四章 曲江池畔听雅集转眼到了暮春时节,
长安城里处处飞花。苏墨莲告诉沈砚之,曲江池畔要举办一场雅集,许多文人墨客都会参加,
让他一起去看看。曲江池是长安有名的游览胜地,暮春时节,池边的柳树抽出新枝,
桃花、杏花竞相开放,景色十分优美。沈砚之和苏墨莲赶到时,池畔早已聚集了许多人。
有穿着锦袍的公子哥,有戴着儒巾的文人,还有几位穿着襦裙的女子,
正坐在凉亭里弹琴作画。“那位是贺知章先生,”苏墨莲指着一位白发老者,轻声说道,
“他可是当今有名的诗人,官至秘书监。”沈砚之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
见贺知章正与几位文人谈笑风生,手中拿着一把折扇,气度不凡。他心中激动不已,
没想到自己竟然能见到唐代的大诗人。雅集开始后,文人们纷纷吟诗作赋。
有人吟诵着自己的新作,有人点评着他人的诗句,还有人现场挥毫泼墨,
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沈砚之站在一旁,认真地听着,偶尔也会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
他的见解新颖独到,很快便引起了几位文人的注意。“这位郎君看着面生,不知师从何人?
”一位穿着青衫的文人走到他面前,拱手问道。沈砚之连忙回礼:“晚辈沈砚之,
自幼在乡野间长大,未曾拜师,只是平日里喜欢读些诗书。
”青衫文人笑了笑:“郎君过谦了。方才听郎君点评诗句,见解深刻,
想必是有真才实学之人。不知郎君是否愿意作一首诗,与我们一同切磋?”沈砚之有些犹豫,
他虽然记得许多唐诗,但自己并不擅长作诗。可若是拒绝,又会显得失礼。他想了想,
决定改编一首现代的诗歌,融入唐代的元素。“那晚辈就献丑了。”沈砚之清了清嗓子,
开口吟道:“曲江池畔柳丝长,桃花落尽杏花香。春风送暖入长安,引得游人醉一场。
”诗句虽然简单,却描绘出了曲江池畔的春日美景,赢得了众人的掌声。
贺知章也笑着点头:“好一句‘春风送暖入长安’,颇有几分盛唐气象。沈郎君若是有意,
不妨多与我们交流,将来定能成为一代才子。”沈砚之连忙道谢,心中却有些惭愧。他知道,
自己只是借了现代诗歌的灵感,算不上真正的创作。雅集过半时,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众人抬头看去,见一队骑兵簇拥着一位身穿紫袍的少年走来。少年约莫十八九岁,面容俊朗,
眼神锐利,腰间佩着一把宝剑,一看便知是权贵子弟。“那是临淄王李隆基,
”苏墨莲凑到沈砚之耳边,轻声说道,“他是当今皇帝的侄子,最近在长安城里很有名望。
”沈砚之心中一凛,他知道,李隆基就是后来的唐玄宗,开创了开元盛世。此时的他,
还只是一位普通的王爷,却已经显露出了不凡的气度。李隆基走到池畔,
与贺知章等人寒暄了几句,便目光扫过众人。当他看到苏墨莲时,眼中闪过一丝惊艳,
随即走上前,拱手说道:“苏姑娘的画技,本王早有耳闻。不知今日能否有幸,
见苏姑娘作一幅画?”苏墨莲微微欠身:“王爷抬爱,民女遵命。”她走到案前,拿起毛笔,
蘸了些颜料,很快便开始作画。她画的是曲江池畔的春日盛景,笔触流畅,色彩明艳,
将池畔的美景和游人的欢声笑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李隆基站在一旁,看得入神,
眼中的欣赏之意越来越浓。沈砚之站在人群中,看着李隆基对苏墨莲的态度,
心中忽然生出一丝不安。他知道,李隆基后来成为了皇帝,后宫佳丽三千,
苏墨莲若是被他看中,恐怕会陷入宫廷的纷争之中。第五章 宫廷风波初现雅集结束后,
李隆基果然对苏墨莲念念不忘,派人送来许多赏赐,还邀请她入宫作画。苏墨莲有些犹豫,
她知道,入宫之后,虽然能获得更高的地位和声望,但也会失去自由,
甚至可能卷入宫廷的纷争之中。沈砚之看出了她的顾虑,劝道:“苏姑娘,宫廷之中,
人心险恶,你若是入宫,恐怕会有危险。不如婉言谢绝,继续留在墨莲斋,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苏墨莲叹了口气:“我也知道入宫有风险,可李隆基是王爷,
他的邀请,我若是拒绝,恐怕会给墨莲斋和你带来麻烦。”沈砚之沉默了,
他知道苏墨莲说的是实话。在唐代,皇权至上,若是得罪了权贵,后果不堪设想。最终,
苏墨莲还是决定入宫。入宫前,她将墨莲斋交给沈砚之打理,叮嘱道:“砚之,我入宫之后,
墨莲斋就拜托你了。你要好好经营,不要让我失望。”沈砚之点点头:“苏姑娘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打理墨莲斋,等你回来。”苏墨莲入宫后,沈砚之便开始独自打理墨莲斋。
他将现代的经营理念运用到画肆的管理中,比如推出定制画作的服务,
根据客户的需求创作个性化的作品;还在画肆里举办绘画培训班,
吸引了许多喜欢绘画的人前来学习。墨莲斋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名气也越来越大。然而,
沈砚之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强烈。他知道,李隆基此时正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政变,
夺取皇位。而苏墨莲在宫中,很可能会被卷入这场风波之中。果然,几个月后,
长安城里便传来了消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了唐隆政变,
杀死了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拥立相王李旦为皇帝,李隆基则被立为太子。政变发生后,
宫中一片混乱。沈砚之担心苏墨莲的安危,多次派人入宫打听消息,
却都没有得到确切的回复。直到半个月后,苏墨莲才从宫中出来,回到了墨莲斋。
她看起来憔悴了许多,眼中带着几分疲惫和恐惧。“砚之,宫里太可怕了,
”苏墨莲坐在案前,喝了一口茶,才缓缓说道,“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死得很惨,
宫里的人都人心惶惶。李隆基虽然成为了太子,但他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恐怕很快又会有一场风波。”沈砚之安慰道:“苏姑娘,你能平安回来就好。
以后不要再入宫了,我们就在墨莲斋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苏墨莲点点头,
眼中露出一丝向往:“我也是这么想的。只是,李隆基成为太子后,权势越来越大,
他若是还想让我入宫,我恐怕还是无法拒绝。”沈砚之沉默了,他知道,
苏墨莲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李隆基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他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能为自己所用的人。接下来的日子,长安城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双方都在暗中积蓄力量,准备最后的决战。
沈砚之担心墨莲斋会受到波及,便决定暂时关闭画肆,带着苏墨莲去洛阳避一避。
苏墨莲同意了他的提议。两人收拾好行李,趁着夜色,离开了长安,往洛阳而去。
第六章 洛阳城里遇旧识洛阳是唐代的东都,同样繁华热闹。
沈砚之和苏墨莲在洛阳的南市附近租了一间小院,暂时安定了下来。
洛阳的风土人情与长安有所不同,这里的人更注重商业,街道上的店铺比长安更多,
商品也更加丰富。沈砚之偶尔会去南市逛逛,了解洛阳的市场情况,想找机会重新开设画肆。
一天,他在南市的一家丝绸店前,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人穿着一身丝绸长袍,
正与店主讨价还价,侧脸看起来很像李阿然。大家打赏求打赏作者谢谢大家,后续,
长安十二时辰·归客行第六章 洛阳城里遇旧识沈砚之快步上前,试探着唤了声:“阿然?
”那人猛地回头,果真是李阿然。只是如今的他,
早已不是平康坊里那个穿着粗布短褐的杂役——锦缎长袍镶着银线,腰间系着玉钩带,
头发梳成了成年男子的发髻,脸上的稚气褪去不少,多了几分精明。“沈郎君?
”李阿然也愣住了,随即露出惊喜的神色,“您怎么会在洛阳?我还以为您还在长安呢!
”两人找了家临街的茶肆坐下,李阿然才说起自己的经历。原来唐隆政变后,
平康坊乱了好一阵,他趁机离开了长安,跟着一位做丝绸生意的胡商来了洛阳。